1977年“十一“休假前,十万人夹道欢迎外宾的盛况出现在北京街头。贵宾是被尊称为“同志”的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。这个年代,被称为“同志”,意味着 是反修反霸斗争中共进退的亲密战友,例如朝鲜的金日成、阿尔巴尼亚的霍查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。一个月前,刚刚与中国修补篱笆前来访华的南斯拉夫强人铁托,也享受了同等待遇。

1977年波尔布特访华,当时的党政军第一号人物华国锋到机场迎接
波尔布特抵京的这一天,我所在的小学的迎宾队还在学校操场上全力以赴地排练新舞码——“铃鼓舞”,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几天后欢送波尔布特和他的代表团。此时我参加迎宾队已有将近两年,也算是一名“老队员”了,但是还是第一次学跳这种有些技术难度的舞蹈。过去两年,我们的迎宾舞大致是一手拿纸制花束,一手拿七色彩带,动作也多是转圈、挥手、跳跃,也没有复杂的队形变化,连我这种严重缺乏艺术素质的人,看一遍也基本上学会了。
伴舞音乐一直是《友谊花开万里香》 ,就是姜文导演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出现过的那首:“美丽的鲜花在开放,在开放,朋友们来自远方,来自远方;亚非拉朋友手挽手,友谊的歌儿高声唱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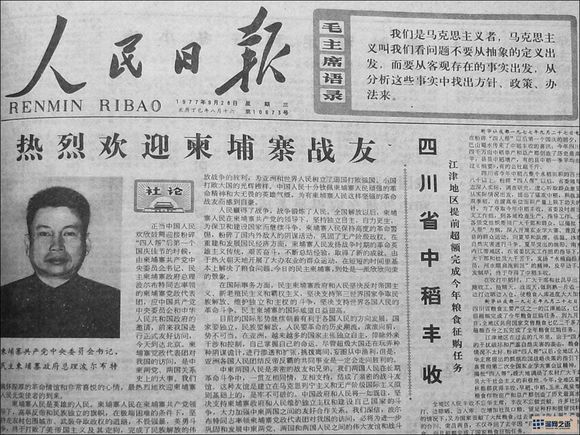
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社论欢迎波尔布特
这回的铃鼓舞却大不相同,要在舞蹈的同时准确地按照音乐节拍,时而摇动鼓身,让铃声响起,时而拍动鼓面,队形变化也比较复杂,要几百人动作节拍完全一致,绝非易事,而我三番五次出错,都被明察秋毫的教练捉到,挨了不知多少训斥,最终别人都回家了,我和其他几个“手脚不听使唤”的队员被留下“加班“,心中不停地暗自叫苦。
刚上小学不久,我就注意到每天放学后占据操场排练的迎宾队。听高年级的同学说,这就是新闻电影上(那时连黑白电视都没有普及)外宾来访时,在机场的停机坪上跳舞欢迎的那群人。只要有外宾来访,迎宾队员便一整天不上课,到位于东北郊外的机场迎送。名正言顺不上学,对于我这种不喜欢上课却不敢逃学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,当舞蹈教练到班上来选人的时候,我特意挺直了后背和脖子,于是如愿以偿。
而进入迎宾队后,第一件事不是练基本功和学跳舞,而是上政治课,提高政治觉悟。
小学的各种社团当中,迎宾队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,因为它承担了国家级外交活动,在“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场合“表演,因此按照教练的话说,我们绝不是单纯地”跳舞“,而是在”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“,肩负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任。
当接到新的迎宾任务的时候,学校广播站就会召集全体迎宾队员到小礼堂上课,除了“要将红旗插遍全球”的伟大愿景之外,还会学习一下外宾所在国的历史地理、风土人情,以及与中国的友好关系,而这个部分,普通的课堂绝不会教,报章杂志上也没有,估计是老师从《各国概况》上抄来念给我们听的,但是能知道一点遥远国度的知识,哪怕都是用伟大领袖“三个世界的理论“解构过的,也让我的小小好奇心得到巨大的满足感,听完课之后,就会用红铅笔在家里的世界地图上标出迎送过的外宾的国家,画上一面小红旗,两年下来,红旗大约有了十几面,都集中在亚非拉地区。
当时的外交活动远不如今日频繁,但是迎宾队的规模却是宏伟壮观的。我所在的一千多名学生的学校,迎宾队就有一百多人。和另外三间小学的迎宾队组成一个四百人的方阵,方阵中除了舞蹈员,还有负责在最后一排组花墙的中学生和花墙之后的中学生军乐队,但这个方阵也不过是整个迎宾活动里的一颗螺丝钉。
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,搭飞机出国跟普通老百姓八竿子打不着,当然,机场也不是供普通人出入的公共场所,它的神秘程度和天安门城楼基本一样。因此,作为迎宾队员,能够经常坐着大巴去北京机场“执行外事任务”,是一件非常拉风的事情。
给予迎宾队的待遇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也是非同寻常的。迎宾的当天,每人可以领到一个干果面包和一瓶北冰洋汽水,都是票证时代的贵重食品。巴士也是那个时代最高端的,墨绿色的捷克进口克罗莎大客车,车椅是真皮沙发,一上车,一种献身世界革命的豪情便油然而生。

迎宾队伍专用的克罗莎大轿车
那时还没有机场高速公路,另一方面整个城市也没有多少机动车,完全不必担心交通阻塞,从市中心出发到位于顺义的机场,驶过只有双向两个车线的“机场路”,还是要大约两个多小时。一出东直门,车窗外能够看到的只有果园和田野,还有在我眼里恬静美丽的温榆河。
或许是好事多磨。第一次迎宾那天,途中发生了小插曲。
教练忽然走到我的座位前,一副命令口吻:“等一下到了现场,你和小英换一下位置。”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令惊呆了,本来我的位置是在第一排,小英在倒数第二排,换到那样的位置,绝不可能清楚地看到“党和国家领导人”和外宾的光辉形象。
教练似乎看出了我的不悦,立刻提高声调:“我们是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政治任务的,首先要服从组织!不然你就别上场,一个人在车里等着!以后也别来迎宾队!“我违心地点点头,没想到教练还有第二个命令:”你把你的毛衣也和小英换过来!“换位置也就罢了,还要换衣服?当时我们的统一服装只有一件天蓝色长裤,上衣都是自己的,当然为了体现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,每个人都穿了自己最漂亮的毛衣,我的那件柠檬黄的毛衣是二姨特意为我手织的,左襟上还用棕色的线绣了一只活泼可爱、正在啃松果的松鼠,整个迎宾队的同学都对这件毛衣羡慕不已。
我忍着心里的失望,跟小英交换了毛衣,那是一件明显用机器织成的大路货,呛眼的绿色,我只感到自己瞬间变成了一只丑陋的青蛙,却不能说出这种感受,只能呆呆地望着窗外,让眼泪流在心里。
过了若干年,我才知道了教练要我和小英换位、换衣的理由:小英的父亲是某部委的军代表,在迎宾队这样高度政治化的团体里,我这样一个来自“臭老九”家庭的孩子绝对不应该站在第一排、更不能穿最靓丽的衣服,而小英才是享有这一切最合适的人选。教练如果欠缺了这样的政治觉悟,肯定离下课不远了。
(待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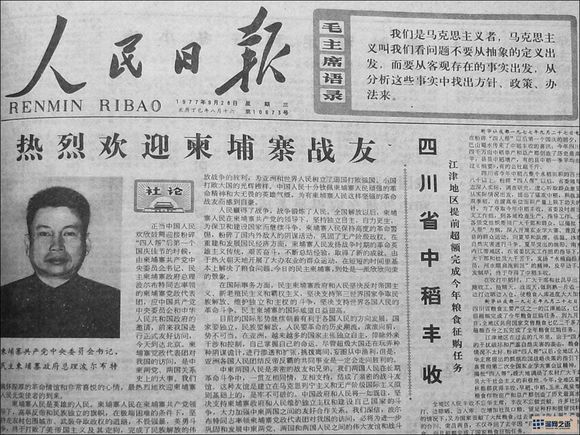
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